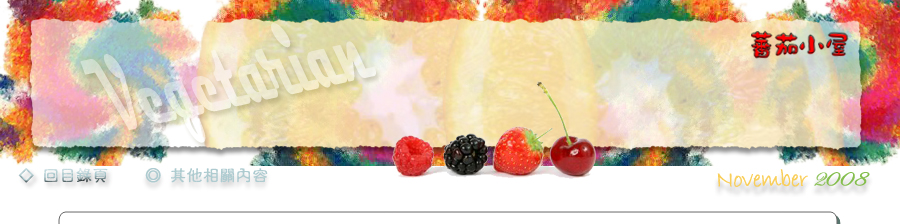|
每次见到司徒的时候他都有两个特征,一是相机不离身,再来就是脸上总带着微笑。位于澳洲雪梨的南天寺,属于汉传的佛教寺院,僧众及信徒多为亚裔,举办的法会活动也都使用中文。司徒在咨询室(information
desk)做义工,他是荷兰人。虽然不懂中文,但却完全没有影响他的工作,反而因为语言及背景的差异,和周遭的人擦出另类的火花。
「人与人之间的互动是超越语言界限的。」第一次见面时司徒这样和我说,「佛法也是。中文也好,英文也好,荷兰文也好,语言只是一个工具,让人们瞭解真理的工具,当我们真正体解了真义,达到了认识,那么运用哪种语言,甚至是否需要运用语言,都无关紧要了。」
「就好比微笑是全世界都通用的问候一样。」我点头。
「当然,如果你和我讲中文,我和你讲荷兰文,到最后我们或许会有共识,但远远不及我们一起用英文沟通来的有效率。」他哈哈笑了几声,「所以虽说语言不重要,但也不能说语言毫无用途。」
多日后,我诵读金刚经时,
忽然想到司徒的这番话,感叹着他已经把般若智慧融入生活,并成功地证实给了身边的人。
司徒退休前是警察,阅人无数,也经历了许多常人无法想象的历练,所以对事物的看法会有独到的见解。他认为人生的意义就是分享和奉献。司徒酷爱旅行,更喜欢用相机记录生命。他把退休后的重心一半拨分在背相机,一半拨分在当义工。来到南天寺,正好让他有机会把两者合为一体。这些年来南天寺重要的法会,都经由他的镜头,拍摄下许多寶贵的记录。
司徒有着圆圆的啤酒肚。远远地,只要看到一个超大单眼相机镜头挂在圆滚滚的身前,并听到爽朗的笑声,大家都知道那是司徒。有位法师某天笑着称他为【Happy
Buddha】,众人才恍然觉得他真的与满脸笑容的弥勒佛有几分神似,于是南天寺各分院的义工朋友们都唤他Happy
Buddha,司徒的笑声穿透力也就更强了。
某天我不慎进食沾有海鲜的汤底,导致严重皮肤过敏,无数痕痒难忍的小红疹,让我坐立难安。当我捧着像蕃茄一样肿起的脸颊唉声叹气时,司徒给了我一个大笑脸。
「你应该高兴才是。」他说,「这说明你是一名注定的素食者
(Vegetarian by Default), 而不是选择性的素食者(
Vegetarian by Choice)。就好像我一样。」
若是有选择的,或许某天我会选择舍弃素食这条路,而若是注定的,那么素食这条我此生都会一直走下去。司徒的安慰让我笑了。
「我对蜜蜂过敏。」司徒告诉我,「如果我被蜜蜂扎了,下一秒钟我就封喉了。」
「这么严重?」我惊讶。
「体质如此。」他对我挤挤眼,「我也是被菩萨挑选过,注定要成为素食者的呢!」
极度敏感的体质,局限着司徒的饮食选择,除了不能进食肉食之外,连花生,牛奶,蚌壳类海鲜,
鸡蛋,麦类 (wheat) , 酵素 (yeast),蜂蜜,咖啡因等等都是过敏原。他的过敏单很长一串,我越听越心惊。
「巧克力也不能吃?」我睁大眼,「甚么?面粉也过敏?」
「一点也不影响我啊。」司徒摸摸自己的啤酒肚,「你看我照样很开心,把自己养得圆滚圆滚的。」
司徒说过敏原好比戒律。很多人听到「戒」就觉得自己是失去了自由,其实非然。有了戒,知道甚么是被建议不要触碰的,并付诸于行动,人生反而更广阔。
「当我知道我不能喝牛奶,我就改喝豆浆。意识到牛奶是让我上吐下泻的原因,就停止去饮用,这样我远离病痛的折磨,难道不算是获得了自由吗?」司徒更深一层的尝试解释他的想法,「受戒也是如此,知道甚么是让自己身心不快乐的,就不要去毁犯,获得的將会是更大的解脱。」
我很认同的。
不久前南天寺开设了佛学课程,法师以中文授课,我在课堂上很惊讶地看到司徒。
「你中文突飞猛进了啊?」我坐在了他身边。
「我只是喜欢上课的环境,这里的气氛很鼓励我。」他说,「看见这么多年轻的佛学弟子,週末不是去逛街玩耍开派对,而是拨时间来这边精进佛法,想到就让我感动。」
但他遇见我了,我就是他的同声翻译。
我把法师在台上讲的话即时打成英文显示在笔记电脑上,他再把他的想法和回应打在他的电脑上。我们听着法师的开示,并在同时展开着激烈的探讨。一切都在无声中进行,但互动是那么的强烈。我在几个瞬间有着深深的震撼,想起第一次见面时司徒说的那番话,语言只是一种形式,而很多东西,是超越形式,以无形的姿态存在着的。
司徒在韩国受五戒,日本受菩萨戒,曾在泰国住过非常久的一段时日。他有许多的机会接触寺院,也和各道场,各宗派的僧众结下深厚的因缘。当他展示历年来在世界各国各寺院与各法师的合照时,我的眼中透露出羡慕的目光。
「我是幸运的。」司徒自己也承认,「我在寺院不仅认识了法师,并认识了许多年轻的义工,他们让我的心永远保持着青春活力,精进不懈。」
说完司徒把右手举在空中,很郑重地指了一下我,「好比妳,从妳身上我看到许多能量,所以不用对我说谢谢,妳也帮了我很多。」
我曾经不止一次抱怨,素肉素海鲜的腥味让我感到阵阵不舒服,所以我都会特意挑出来,拜托身边的朋友帮我吃掉。有天司徒喝完碗内最后一口汤,然后对我说,
「妳吃素,是因为身体不能接受肉味,对不对。」
我点头。
「所以妳吃到素的肉,因为有肉味,所以感到不舒服,对不对。」
我再点头。
「但妳如果告诉自己,那不是素鱼,那只是香菇蒂;那不是肉味太浓,那只是菜味太淡;那不是假的肉,那其实是真的菜。妳心里还会不舒服吗?」
我歪了一下头思考着。
「因为妳心中不停告诉自己,那是一块有肉味的素食。一旦心里坚持着这个想法,就开始把对肉的厌恶投射到这块素菜上。于是吃在嘴里,烦到心里,越咀嚼越不舒服。」
我又点了一下头。
 「尝试着不去想,自己夹着的是假的肉块,飘着的是真的肉香。不要起分辨心,不要起喜恶心,妳吃在嘴里的只是一块食物,是给妳这付色身皮囊的药,让进食后的妳,有力气去学更多的知识,有精神去做更多的贡献。不管是甚么味道,喜欢或不喜欢,都让自己去欣赏,而不是平白无故的给自己增添不必要的负担。这样妳打饭的时候不会罣碍碗中会不会有素肉,吃在嘴里的时候也不会介意是不是有肉味,挣脱了自己给自己强加的所谓不吃素肉的框框,妳吃素的道路会走得更自在。」
「尝试着不去想,自己夹着的是假的肉块,飘着的是真的肉香。不要起分辨心,不要起喜恶心,妳吃在嘴里的只是一块食物,是给妳这付色身皮囊的药,让进食后的妳,有力气去学更多的知识,有精神去做更多的贡献。不管是甚么味道,喜欢或不喜欢,都让自己去欣赏,而不是平白无故的给自己增添不必要的负担。这样妳打饭的时候不会罣碍碗中会不会有素肉,吃在嘴里的时候也不会介意是不是有肉味,挣脱了自己给自己强加的所谓不吃素肉的框框,妳吃素的道路会走得更自在。」
司徒的话让我想了很久。到最后我忍不住还是写了封信致谢。
「碗中有素肉就吃,没素肉就不吃,遇到不喜欢的就包容,遇到喜欢的就感恩,很多事情,也就是这样了。」我的感触,一字一字地敲在键盘上。
「说过几次了,不用谢我。」司徒回信的时候连打了好几个哈哈哈。「我只是表达我的想法而已,真正在执行,在实践,最后在受益的人,还是妳自己啊。」
三个月前的某天,司徒告诉我他会离开一阵子。
「我要去旅行了。」他这样说,「先去新加坡,再去越南,韩国,日本,英国,西班牙,阿根廷,南极,还有好多我暂时想不起来的地方。」
「行程真丰富。」我叹一声。
「我快七十了,最近身体不好。」司徒说,「在还能四处逗留的时候,我想再去一次曾经感动过我的地方,和曾经感动过我的人好好说声谢谢。」
我的眼中闪过一丝哀伤。
他立刻对我开怀大笑着,「妳别舍不得我啊!我会寄照片给妳的。」
陆陆续续地,我的信箱中出现着司徒的问候,显示着各个城市不同IP。他用镜头捕捉着眼睛所想珍藏的片段,新加坡的车站,越南的河畔,柬普寨的浮雕,韩国的钟楼,尼泊尔的夕阳,日本的寺院,阿根廷的极光。信中总是简短报着平安,并告诉我相片的内容和故事的背景,却从来不提他的下一站在哪里,也不说会在哪个地方停留多久。司徒说充满期待的人生,是最美好的。
我等着某天信箱中出现雪梨机场的照片,这样我就知道,过不多久我就可以再见到他,总是带着微笑的Happy
Buddha,健康平安的和我一起探讨分享感触感受。 |