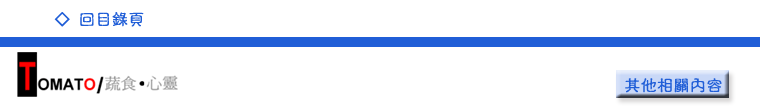朋友傳給我一幅花圖,讓我猜猜是什麼花。那花有狹長形的綠葉子,中有小花蕊。
 我一看,脫口而出:是茼蒿。 我一看,脫口而出:是茼蒿。
朋友捂著嘴笑:也算是蒿吧。
再三追問下,才知這花原來是野菊。野菊算是凡物,所以從來只記得花瓣而疏忽葉片。
後來一查,茼蒿也屬菊科,別名菊花菜、春菊。
《本草綱目》曾記載:“九月份下種,冬季及明年春采食,莖葉肥嫩,微有蒿氣,故名茼蒿,花深,狀如小菊花。”
而蘇東坡有詩雲:“漸覺東風料峭寒,青蒿黃韭試春盤。”蘇東坡這句詩中的“青蒿”,指的也是茼蒿。
湖南的蔬菜多而嬌美,選擇性大。茼蒿有季節性,且不起眼,故吃的少。
而我原本不愛吃茼蒿的,嫌它的那股清氣,有點嗆鼻。今日想來,那時年少,不會做料理,許多好的蔬菜在我手下想來也甘於只要熟了便好的命,被我糟踏了好些年。世上沒有不好的食材,只有不精的手藝。倘只手巧,而心不靈,那菜必定也只是二流之味,真正的美食該是暖人心,帶來幸福快樂的。
這樣想著,突然對茼蒿生出無限的好感來,坐車直奔超市。
陽光很重,似是六月天,我提著兩把茼蒿,一路流了不少汗。
噴著水霧的茼蒿鮮嫩水靈。一根根嫩葉交替叢生。拿在手裏,輕巧似豆腐。
喜歡摘菜,仿佛置身於綠色仙境。菜根有黃土,摸著很踏實。某日之時我們也將與大地彙集於一體。與這些蔬菜們在地底下相親相愛。有時會嚇一跳,菜葉裏跑出了一個幾隻腳的蟲子。在水裏遊來遊去,這一池似是它的家,它清閒得很。
清炒的茼蒿,一會兒就軟成一團水汪汪的。
涼拌的茼蒿,淋些香油,撒點鹽粒,便成上好涼菜。
海南人喜歡將此菜下火鍋吃,說是去油膩極好。
唐代醫學家孫思邈在《千金方‧食治》中說,吃茼蒿可以“安心氣、養脾胃、消痰飲、利腸胃”。原來是有道理的。
《本草逢原》上說,“茼蒿氣濁,能助相火,多食動風氣,熏人心,令人氣滿”,故一次不可吃得過多。可是吃起來時,今日不記昨日,誰又記得這些前人說過的話呢。
記憶最深的是朋友與茼蒿的相遇頗有發思古之憂。他說:“只要吃茼蒿,便會無來由地想到陳子昂的“登幽州古台”:前不見古人,後不見來者。念天地之幽幽,獨悵然而泣下。”我暗笑不已,卻引發了他兒時的回憶:“有一次因為我父親為了我晚上和大孩子們出去打鳥,回來晚了不讓我進門。那是個初夏的時分,半夜開始下瓢潑的雨。我蜷居在家門口的一隻紙盒裏,被蚊子叮咬得無法入眠。想起了早逝的母親,就決定離家出走。那時我剛剛十一歲。居然徒步跋涉了兩百多公里,兩天後到了姑媽的家。知道路上餓了的時候我吃的是什麼嗎?盤龍生,苦澀的青杏和路旁溝邊的茼蒿!那時的夜晚真安靜,月亮和星星也真明亮。而我一點也不害怕。我一路走,一路為自己編各種各樣的故事。想像自己是那些古書裏的人物,手裏握著樸刀,長劍什麼的。你知道嗎?就那樣生吃茼蒿,那股濃烈的味道真難聞!但路邊野生的玫瑰花瓣,還有野生的苦瓜和草莓的味道讓人難以忘懷。”朋友的話讓我無語。原來茼蒿與菊相親,骨子裏該是有野性之美的。
有一日看星座與花語,查了我的生日花,是白菊花,由此真的喜歡茼蒿了。
|